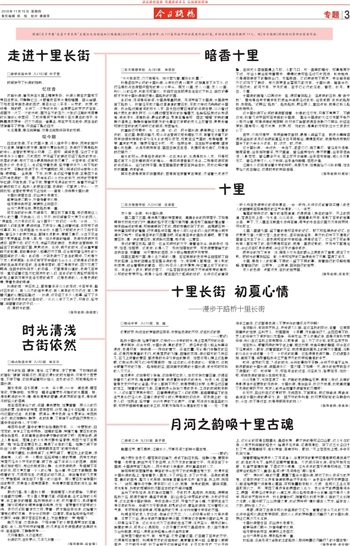翰墨流芳,清风拂煦,江南水乡,尽享月河之韵唤十里古魂。
——《题记》
鳞次栉比古老宅,错落有致白黛瓦,逶迤不断石板路。恬静淡雅,青丽中带着一缕思绪,映出岁月不老容颜,似风云犹存的南官女子。月河孕育了十里街,十里街养育了路桥人,两千年的斗转星移,使我重温古时人文。
暖阳照射到屋檐棱角,黄昏的序头拉开了我的唤醒古魂之旅。我漫步在十里长街的路上,端详着老人面庞,少了许轻狂,多了份安逸。沿街的明清屋,精致的窗秀,整齐斗式吊楼,样样彰显着当年流传“庙对庙,桥上市,阴阳水。”一刹那,嘈杂与宁静,原来可以这么近,就是一转身的距离。望向河面,波光粼粼,折射的斑斓将我沉醉在古时的热闹与喧嚣。
金兵灭宋势如洪,赵构难逃落帽风。于此机缘,路即桥,桥即路,便赐有路桥之名,起源于南宋,鼎盛于明清。在《山海经》中零碎的记载,多数记于贸易,这也正是十里的特色。号称古街分三段,开端为饮食小铺,为居民生活交易买卖的场所。中间为女子服装街,时髦的设计,摩登的装饰,充斥着现代化气息。末尾则有海洋味道,那是渔民的交易,似乎诉说着千年来的历程。
听闻住那的老人家口述,每逢这农历三、八,人们总是会起个大早去赶集。买累了之后,便会来碗热腾腾的姜汤面,只要有这老牌姜汤面的名号,客人总是络绎不绝。这似乎也成为了古街的生活习惯,流传至今。喝完这暖心暖胃的姜汤,可未必心满而归。小孩子喜欢去那文昌阁读书,老人自然是去戏台听越剧,年轻人便赶往快船埠头进行渔市生意。
在房屋交错的地方,有一簇茂盛,它象征着这里,它目睹了百年的历史,它便是那古樟树。听闻是苏家的远祖种的,寓意着生意兴旺,各辈香火薪薪相传。忽然明月升起,我不舍离开依旧停留于此,似见五桥月夜,交谈于桥上,这谈论的可是右君墨池,昌阁书声。最欢快的是那泾口山歌,这儿水流较急,从卖芝桥向南的船老大,摇得汗流浃背,还得用绳拉。到了这三水泾口才松了气,便提高嗓子,拖长声音,非常好听。歌曰:“天上落雨地上斑,手中无钱到处难。”
随着歌唱摇曳便步入了月河渔火,华夏民族的勤劳可谓是展现得淋漓尽致,皎洁的月光下,渔民还在操劳着捕鱼。冬夜闲行到水滨,河如弓样月如银。松堂茭首塘桥蟹,下酒依然乡味真。红光点点的屋子便是那诗社,文革结束后的路桥文人重组《潞河》使“月河诗社”得以继承。
“哎”一声长叹,响彻云霄,震醒了整条十里长街,撼动了我心底深处的灵魂。这非物质的文化传承难道就要命尽于此吗?!徐老在长街开家锡器店,以前结婚锡器六件套是必需品,可现销量越来越少,反被一些现代工业化用品取而代之。另一原因又是传承做锡器的人也少。老派手艺做锡器是纯手工,锡器一般要经过复杂的10道工序,而价格却卖得十分低廉,自然是没人来学,导致手艺即将失传。我也跟着长叹,随着现代科技发展,以前的文化也随之流散,心里升起了丝丝惋惜之意,我欲想呼吁“请珍惜古人艺术,留存古人之物,倾听古人之心。”
一晃眼,便到了古街与现代中盛街的交汇处。看着这古今文化的交织,也许中盛现代街正繁荣而起,但我从心底的想唤醒这沉睡已久的十里长街,想让它再次风水流转。
十里长街昔日容,依山傍水走神龙。
邮亭驿递汉朝令,妙智寺敲宋代钟。
话月巷中新市客,粜糠桥上老田农。
台州六县繁华地,要数路桥第一重。
我坚信,流淌月河之命脉的土韵路桥人即将唤醒这沉睡已久的十里古魂!
(指导老师:牟玲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