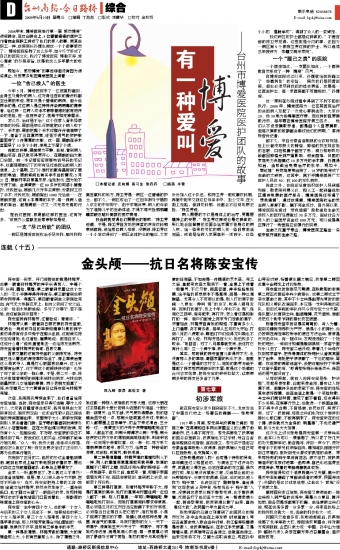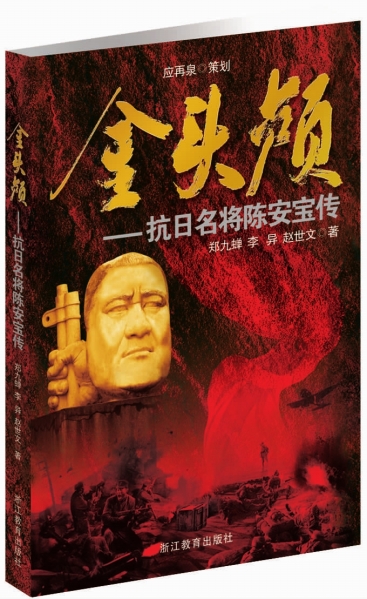陈安宝转向林梅芳,红着脸说:“谢谢你。”林梅芳从第一眼看到日思夜想的陈安宝起,就被他一身威武夺目的军装和精神抖擞的样子激动得像有许多只兔子在胸头乱跳,这时候见陈安宝说谢她,也红着脸,腼腆地说:“都是自家人,还说什么谢?”说完,害羞地去一边给陈友廷煎药。陈安宝看着林梅芳的背部,百感交集。
百感交集的还有陈安宝的父亲陈友廷。陈安宝已经从著名的保定军校毕业了,穿上军装后竟这么英武夺人,真是打心眼里感到高兴,这儿子就要有出息了,还不乘这个时候快快成亲?也好了却了做父亲的一桩心事。于是,第二天一早,陈友廷就撑着瘦弱的病躯来到林伯明家,与林伯明商量两家儿女结婚的事情。两个老朋友掐算了一阵,决定腊月二十六黄道吉日让陈安宝与林梅芳完婚。
次日,马院陈氏房族全来了,他们准备给陈安宝结婚。当时,陈安宝家穷得叮当响,要什么没什么,大家就商量着凑合起来,新房用具由大家拼凑而成,婚床预定由一位叔伯兄弟从自己刚结婚的房间里腾出来。家里房子太小,弟弟安民就到别人家去借宿几晚。至于喝的喜酒到时候想办法从小店里赊帐。正在大家出谋划策的时候,突然有个人一拍脑袋说:“不对呀,安宝娘的忌日不是快到了吗?按我们这儿的风俗,过年前不能举行婚礼啊。”众人一听,恍然大悟,连连点头称是,都说怎么就忘了呢?陈友廷便决定过了正月初八再为他俩举行婚礼。
然而到了正月初二,路桥的於达坐着船到横街,跑到他家说上峰打来电报到许植怀家,要他们四位立刻起程回部队,战争马上要爆发了。
全家人一听,都楞住了,怎么就这么不凑巧?正准备结婚呢。但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岂可不听命令?当天,陈安宝把身上带的工资(军饷)全部交给林梅芳,毅然决然地走了。一直走到路口,他才回过头望了一眼自己的家,发现林梅芳还依依不舍地站在门口目送着他。一股酸楚的味道涌上陈安宝的心头。
陈安宝一生中有四个女人,他的第一个女人与后来的三个女人完全不一样。如果说他的第二个女人是洋葱,第三个女人是辣椒,第四个女人是苹果的话,那么林梅芳就是台州山里出的一块番薯,她虽然不识字,但却有三样拿手的手艺。
第一样是做蒲扇。林梅芳做的蒲扇,大的有桶盘那么大,小的有巴掌那么小。除了蒲扇之外,她还做一种别人很难做的方形大扇。这种大扇在过去是路桥十里长街剃头店里的专用品。十里长街一到夏天,台风不刮,天气便热得要命。别的店铺尚且好说一点,那剃头店简直没法过,来剃头的人都要围上白布单子,初坐下来还凑合,三分钟一过,一身黄豆大的汗珠子便劈哩啪啦地往下掉。人都坐不住,叫剃头师傅怎么剃?于是,剃头店便把这种方形的蒲扇高高地挂起来,叫徒弟站在一边用绳子牵着拉着。这一牵一拉,那方形大蒲扇便摆动起来,凉风习习,给顾客一种舒适的凉意,或刮脸,或掏耳,畅快淋漓。
第二样是编草帽。林梅芳编的草帽和别人不一样,别人的草帽用席草编起来就完事,她编的草帽不仅要打上蜡,而且还用光滑的鹅卵石一点一点地砑平。做好之后,拿起来一看,那帽子表面熠熠发亮不说,而且非常挺刮,拿到街上去卖,总能卖个好价钱。
第三样是打草席。别看林梅芳年龄不大,却是打草席的高手,她打的草席与村里任何一位妇人都不一样。别人打草席,一年可以劈哩啪啦、劈哩啪啦地打到头,而她打草席用料要求非常高,草必须是五月初五烈日当空时割下来的好席草,必须是当日让毒日头把它晒干,用的短草、小草不饱满不圆滚的不要。她精心挑选那种色青、身圆、有香气的席草。马院村里别的女人一天下一领席子,独有她五天六天才下一领席子。并不是她动作迟缓,而是她用心极细,每一根席草必须到了最佳处才肯下席档。她打的席子与其说是平常的日用品,不如说是一件精湛的艺术品。完工之后,拿起来放在太阳底下一看,全席上下透着一股碧气,不仅匀称,而且密匝,伸手轻轻地抚摸,给手指的感觉根本不是草席,而是一种丝绸制品。尤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别人打的席子时间一久便生一种叫“夷”的虫子,咬得人周身发痒。而她打的席子,放上十年八年也不生“夷”,连用它三四年,卷将起来,再打开,怎么看还是和新打的一样,用户们都爱上陈家专门定做的席子。尽管如此,林梅芳自有她的规矩,不管有多少人上门催要,决不肯多做。每年从五月初九开始,打到八月初八便歇手,哪怕订户们说得龙叫唤也不再打了。有人说:“林梅芳是官太太,她怕钱多了咬手。”她回答:“过了八月席草就变质,我还打它有什么用?立一个牌子难,毁一个牌子易。”
其实,那时候的陈安宝官儿做得并不大,也没有那么多的军饷,寄回家里的钱也不多。但就是这么一个普通的农村女人,用她的勤劳与能干撑起了陈家那两间破旧的木屋;就是这个地道的台州农家姑娘,把陈安宝的弟弟拉扯大,让患痨病多年的陈友廷多活了几年。
第七章
初涉军旅
就在陈安宝从家乡回到部队不久,北京发生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场著名的闹剧——“张勋复辟”。
1917年5月间,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府院之争”在英美和日本两派帝国主义的怂恿下愈演愈烈,已斗得不可开交。黎元洪罢免了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段祺瑞也不甘示弱,号召各省督军脱离总统管制,宣布独立。黎元洪于是密召安徽省督军张勋入京调停,而段祺瑞认为自己可以拉拢张勋,也支持其入京。
这张勋是何许人物?他可是个特别的另类,早年镇压过义和团运动,为清廷立下过汗马功劳,武昌起义爆发后,他站在革命的对立面,虽然被打败,却丝毫没有革新之意,反而禁止他的士兵剪掉辫子,示意效忠满清,因此,他的部队被人称为“辫子军”。也许正应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句老话,6月中旬,张勋统五千“辫子军”入京,没想到这老家伙既不帮黎元洪,也不帮段祺瑞,反而各打了他们五十大板,与一帮遗老遗少一起,拥进紫禁城,把废帝溥仪搬了出来,宣布“奉还大政”,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
张勋复辟的丑剧立刻遭到了全国民众的强烈反对,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号召各省革命党人联合出兵讨逆。浙江督军杨善德是安徽人,受段祺瑞指派,在浙江本无根基,又是棵墙头草,段祺瑞号召各省独立,他就宣布独立,后来见形势不对,又随大流取消独立,现在孙中山号召讨逆,杨善德也随之响应,浙军第二师因此奉令出师北上讨伐张勋。
陈安宝这时刚刚见习期满,在张载阳的浙军第二师正式担任步兵少尉排长。这第二师成立于辛亥革命之时,其中不少士兵是由原光复时的敢死队和义勇队改编而来,本应是一支叫得响的部队,但旧式军阀的军队作风令陈安宝十分失望,连队里从长官到士兵,酗酒赌博,花天酒地,谁都没把这个新来乍到的排长放在眼里。
别看陈安宝平时总是笑呵呵的,与人为善,但到关键时刻却极为严厉。虽是小小的排长,他仍按照在保定军校所学的德日方法治兵,常常星夜突击点兵。有一回点兵,发现独独缺了一个姓张的班长,一询问才知道是躲到县城一家窑子里找乐儿去了。陈安宝二话没说,带着几个兵连夜找到那家窑子,把赤身裸体的张班长从香窝窝里揪了出来,用枪把子狠狠敲了一下他的脑袋,骂道:“你他娘的再敢逛窑子,我把你脑袋拧下来喂了这窑子里的狗。”吓得那张班长连连点头,连回话的勇气都没有了。
从那时候起,就有人说陈安宝是张“护法相”,笑起来像弥勒,凶起来像金刚,着实让人捉摸不透。但据许多他的老部下说,陈安宝的性格其实很好捉摸,他在生活上就是一个笑脸弥勒,与士兵们同甘共苦,谁见了都不害怕,还会得到不少关照;在军事行动上,他就像一个铁面金刚,来不得半点含糊,不管是谁,该罚该打,照责不误。过了一段时间,那些士兵们也对这个矮胖的排长心服口服,不敢再胡来了。陈安宝所在的这个排,很快就成为全连的“明星排”,不光纪律严明,战斗力也大大加强。
这次北上讨伐张勋是陈安宝第一次带兵实战,他本以为可以一展拳脚了,所以花了好几天的功夫整顿军纪,勤奋操练,待到一声令下,便好带着手下的弟兄们冲锋陷阵。哪知部队刚刚开拔到江苏境内,就听到先头混成旅凯旋的消息。原来那张勋的辫子军徒有虚名,很不经打,被段祺瑞组织的北京讨逆军一击即溃,自己也逃至荷兰使馆保命,荒唐的复辟闹剧就此收场。
陈安宝得知这个消息既高兴又失望,高兴的是历史车轮碾碎了复辟倒退者的美梦,民国保住了;失望的是这仗过早结束,让他这个“武痴”没了用武之地。
随师回到浙江驻地,陈安宝又带领他的一排士兵投入到严格的训练中,虽是炎炎夏日,挥汗如雨,但各项操练都毫不松懈。他经常跟士兵们说,现在训练多苦一分多累一分,将来在战场上的胜利机会就大一成,活命的机会也大一成。
民国风云诡谲多变,张勋被赶跑后,段祺瑞独揽了北洋军政大权,却拒绝恢复国会,并对南方虎视眈眈,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孙中山为维护《临时约法》,决定在南方另行召集国会,组织临时政府。